無氧挑戰人體極限?因個人名譽犧牲弟弟性命?紀錄片中撕逼?堪比年度大戲啊!
原標題:無氧挑戰人體極限?因個人名譽犧牲弟弟性命?紀錄片中撕逼?堪比年度大戲啊!
無氧登頂珠峰的兩個人備受質疑
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並不買萊因他們的賬。其他五個曾經在1953年與丹增諾蓋和埃德蒙·希拉裡首登頂珠峰的夏爾巴人也一樣,他們這兩個歐洲人爬得太快瞭——他們連氧氣都沒有用,這不可能是真的。
1978年5月8日,33歲的意大利人梅斯納爾和35歲的奧地利人彼得聲稱無氧登頂瞭珠峰,他們表示自己是從25938英尺(合約7905米)的南坳5號營地出發,沖擊海拔29035英尺(合約8848米)的頂峰——這意味著,他們通過珠峰和洛子峰之間艱險的南鞍地段隻用瞭8個小時。接著,他們在頂峰隻待瞭15分鐘,然後分別下撤。下撤時間彼得用瞭1小時,而梅斯納爾則用瞭1小時45分鐘。
當這對搭檔返回4號營地時,遇到瞭在這裡等待的隨行英國攝影師埃裡克·瓊斯(Eric Jones),他們通過無線電向在珠峰大本營的紀錄片導演利奧·迪克森(Leo Dickinson)通話。迪克森正在籌備一部關於此次探險的紀錄片《Everest Unmasked》, 這部影片預計將在第二年上映。“我也覺得有些不對勁,”瓊斯說,“他們居然這麼快就回來瞭。”在6月17日的路透社報道中,丹增和其他人告訴記者,他們對梅斯納爾和彼得的登頂相當質疑。
兩位當事人早就料到會有人質疑——在珠峰峰頂時,梅斯納爾為他們自己留下瞭照片,這個登頂證據似乎確鑿瞭。但另一項他們需要證明的似乎就顯得證據不足:那就是他們到底是否使用瞭氧氣。彼得在他1978年的書裡《孤獨的勝利》 《The Lonely Victory》 中寫道:“某些專傢聲稱他們已經找到瞭一些蛛絲馬跡。”對於丹增諾蓋和其他懷疑者的聲音,梅斯納爾在返回意大利後也進行瞭猛烈的反擊:“他們這純粹就是羨慕嫉妒恨。”他告訴路透社:“他們不能理解有人能夠做到他們無法做到的事情。”
但當時許多人並不知曉的是,盡管梅斯納爾和彼得取得瞭史詩性的成就,但兩人的關系卻在漸漸地疏遠,珠峰的“公平登頂”正是他們之間的障礙所在。梅斯納爾和彼得共用一條繩子,但他們隻一起使用瞭很短的一段時間,其他的時候,他們都在自顧自地以無保護攀登和無氧的方式向上爬。盡管兩人之間的溝通甚少,在1978年春天的那個瞬間,他們還是一起站在瞭珠峰峰頂,見證瞭這個人類攀登歷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刻。
梅斯納爾(左)台中通馬桶價錢和彼得在新德裡,從尼泊爾返程的路上
梅斯納爾和彼得登頂一座座高峰,下一步就是“無氧攀珠峰”
在上世紀70年代,登山者們開始漸漸地將註意力從“追求所攀高峰數量”轉移到“追求攀爬路線和方式”上來。1963年,霍恩賓和安索爾德完成瞭珠峰西脊新路線的首登。雖然他們使用瞭氧氣,但他們快速而輕便的攀登方式不僅提升瞭登山的水平,也為整個業界帶來瞭爆炸式的影響。在隨後的十餘年中,這種攀登方式迅速演變成為引領潮流的登山模式,之前盛行的大規模的圍攻型喜馬拉雅式登山模式逐漸消失。但氧氣的輔助依然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攀登珠峰上。
在1975、1976年間,如果你問起任何一個曾經嘗試過喜馬拉雅式攀登的人,“什麼會成為登山的新潮流時”,他們會說:“無氧攀登珠峰。”
“無氧登珠峰”,顯然,梅斯納爾和彼得就是最佳人選。梅斯納爾的外表狂野,他常常綁著頭帶,毛茸茸的大胡子和棕色的蓬松卷發讓他看起來像一隻野獸,當時他已經有瞭豐富的阿爾卑斯山的攀登經驗,在歐洲也已經聲名鵲起。而彼得則看起來幹脆利落,高高的顴骨和閃閃發光的白牙讓他看起來像一個精英人物。彼得攀登的時候常常會揣著妻子和年幼兒子的照片,梅斯納爾則剛離瞭婚。
2017年7月,彼得度過瞭他的75歲生日,與梅斯納爾相比,彼得是一個內向的人。而梅斯納爾以性格急躁並且直言不諱著稱。“他是處女座,喜歡招搖,而我的性格則不喜形於色,喜歡一個人獨處”。彼得在《孤獨的勝利》中寫道:“我們不是那種通常意義上的朋友,我們也不是那種患難與共的兄弟,我們很少向對方談及自己的私人生活。”
從1965年開始,在意大利的多洛米蒂地區,22歲的彼得和20歲的梅斯納爾相遇,開始瞭搭檔攀登,這一攀就是13年。剛開始,他們隻是關註於高難度的攀巖而並未涉足登山。1969年年初,他們兩人加入瞭一個安第斯山的遠征隊並且完成瞭秘魯的第二高峰耶魯巴哈峰東坳的首登,這也是他們初次登上高海拔。
這次登山激發瞭梅斯納爾對於高海拔登山的興趣,他渴望爬更多的山。1970年,他加入瞭一支德國登山隊,他們的目標是攀登海拔26660英尺(約為8125米)的巴基斯坦南迦帕爾巴特南壁的“魯泊爾巖壁”。由於當時彼得因故不能加入,梅斯納爾推薦瞭自己的弟弟岡瑟( Günther )作為登山隊的候補隊員。精疲力竭和患有嚴重高反的岡瑟在那次登山中莫名失蹤,梅斯納爾認為他的弟弟應該是在下撤途中死於一場雪崩(他的遺體直到2005年才被在冰川中發現)。直至今天,梅斯納爾仍認為那次極度艱難的攀登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次,但岡瑟的死把他困在“因個人名聲而犧牲瞭弟弟”的譴責中至少幾十年,在發現岡瑟遺體前,他一直在試圖自證清白。梅斯納爾在山上努力尋找瞭弟弟一夜,從南加帕爾巴特峰下來以後,梅斯納爾曾跌跌撞撞地走到附近的一個村莊求助。就是這次攀登,使他遭受瞭巨大的精神打擊並失去瞭七個腳趾。1974年,梅森納爾和彼得在不到十小時的時間內就征服瞭瑞士艾格峰北壁路線,時間僅用瞭前人記錄的一半。次年,兩人又攀登瞭海拔26509英尺(約為8080米)的加舒佈魯木峰Ⅰ峰,這次他們不僅是無氧,也沒有用任何背夫或建立傳統式的用於儲備物資和前進營地。
1975年,加舒佈魯木Ⅰ峰的攀登結束後,梅斯納爾和彼得在回傢的飛機上用加瞭湯力水的杜松子酒慶祝成功,在他的書中,兩人有一段這樣的對話:“下一步咱們去珠峰”,彼得補充瞭一句:“無氧。”“嗯,無氧,”梅斯納爾點頭同意。
20世紀50年代後,珠峰已經被視為一個擁擠不堪的高峰。
在過去的許多年裡,無氧登珠峰被視為從生理上不可能實現的任務。正如梅斯納爾在2006年告訴美國《國傢地理》雜志的那樣:“這就像是你去登月而不帶氧氣,這怎麼可能呢?”在德國,至少有五位醫生在電視上循循誘導觀眾,告訴大傢他們能夠證明無氧去高海拔根本就是癡人說夢。
這個說法最有趣的地方是:急著做出否定結論的正是登山者自己。事實上,很少有醫生或科學傢就專業角度提出反對,1978年的高海拔研究似乎也與這個不可能的見解自相矛盾。
在1960年至1961年的冬天,為瞭研究高海拔人體生理的反應,埃德蒙·希拉裡率領一支科學團隊在尼泊爾進行瞭一次全方位的遠征考察,十名科學傢花瞭六個多星期在海拔19000英尺(合5791米)的一個管狀膠合板的實驗室內對人體在極限環境下的細微變化進行各種研究。研究發現,喜馬拉雅山區的氣壓比預想的要高,這意味著珠峰峰頂的氣壓或許與海拔27500英尺(約為8382米)的類似。
1977年春,迪克森和梅斯納爾曾在尼泊爾加德滿都租瞭一架單引擎螺旋槳飛機圍著珠峰峰頂飛瞭一圈,當時迪克森和飛行員都戴著氧氣面罩,而梅斯納爾則坐在後排啥也沒有戴。“他的嘴巴發烏,眼睛也瞇起來瞭,但好笑的是,就算是這樣,你也沒辦法阻止他嘰裡呱啦地說個不停。”“當然,在3萬英尺(約為9144米)的高空不用氧氣並不能證明我們可以無氧登珠峰,”迪克森在他的紀錄片中說,“這隻能證明我們可以待在那裡不會被憋死。”
1978年,當彼得和梅斯納爾到達喜馬拉雅山時,珠峰已經被登頂瞭59次,從那個年代看來,這是一個瞭不起的數字(到2017年,已有超過600人登上頂峰)。20世紀50年代後,自從純潔的珠峰被人類征服後,各種品牌商、大量的媒體和自命不凡的登山者紛至沓來,珠峰甚至進入瞭特技表演時代:1971年,日本人三浦雄一郎(Yuichiro Miura)穿著一對雪板,用降落傘控制速度從珠峰的洛子峰一側滑下。他不僅幸存瞭下來並且至今保持著最年長者登頂珠峰的紀錄(他於2013年在80歲高齡登頂瞭珠峰)。
從那時起,珠峰已經被視為一個擁擠不堪的高峰。它的擁擠使得尼泊爾政府決定大本營每次隻能待一支探險隊:前提是位置必須提前預訂,你必須要獲得登峰許可證。1978年,梅斯納爾和彼得參加瞭由因斯佈魯克向導和企業傢沃爾夫岡·納爾茨(Wolfgang Nairz)率領的探險隊,沃爾夫岡希望能把第一個奧地利人送上珠峰。作為一個無動力滑翔翼愛好者,沃爾夫岡甚至把兩架滑翔傘拖到瞭珠峰大本營,他計劃著讓夏爾巴人把滑翔翼拖上珠峰,後來他很快就意識到這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梅斯納爾和彼得毫無疑問是探險隊的中心人物,兩人從德國雜志《GEO》那裡得到瞭額外的資金,並且帶來瞭紀錄片導演迪克森和攝像師埃裡克·瓊斯。這次攀登在登山圈和奧地利廣為人知,但因為梅斯納爾和彼得在世界上還相對寂寂無聞,因而世界媒體鮮有報道。在英國,導演迪克森正在拼命征得制作人的同意,而在美國,他們則幾乎無人知曉。
攀登過程中的撕逼 精彩程度不亞於天使之路
1978年3月,兩人抵達瞭尼泊爾,在到達大本營時,他們首先的任務是找到一條路線通過昆佈冰川。他們兩人都一致同意在這個極端危險的地區放棄用攀登的方法通過,而改用奧地利傳統的方法。梅斯納爾和彼得為進入冰川開路,而夏爾巴人則將鋁梯架在冰川上。
4月20日,雨雪交加的天氣終於停止,梅斯納爾和彼得意識到,如果他們想要登頂就要馬上出發,他們離開瞭大本營。4月23日,饑腸轆轆的兩人到達瞭3號營地,彼得吃瞭一罐沙丁魚,他立馬覺得說不出的惡心,“我直冒冷汗,唾液在我的舌頭下聚集,”彼得回憶,“我想嘔,喉嚨像火燒一樣難受。”他被腹瀉和嘔吐纏瞭差不多整整一晚上。“情況不太妙啊,”彼得告訴他的同伴,“我沒有辦法再往前瞭,你也應該就此返回。”同伴的情況不妙,順帶著天公也開始不作美,一場暴雪眼看著即將來臨,情況變得很糟糕。
到瞭第二天早上,彼得恢復瞭一些,他可以下撤瞭,他花瞭好幾天的時間才恢復過來,(但他仍然不得不吃沙丁魚,迪克森也討厭吃它們:“我說,夥計們,我們為什麼要在珠峰上吃他媽的沙丁魚呢?我們沒有蔬菜湯喝?”)由於同伴的下撤,梅斯納隻能帶著兩個夏爾巴人——明瑪(Mingma)和安· 多傑(Ang Doje)繼續在暴雪中前行,嘗試無保護登頂。但當一行三人嘗試在南坳搭建4號營地時,遭遇瞭一場更加猛烈的暴風雪。他們不得不縮進帳篷裡,任由狂風以80英裡(約為128公裡)每小時的速度掠過帳篷。
梅斯納爾將此時他與大本營的無線電通信對話寫進瞭1979年出版的書裡。“我們的帳篷都快要被吹走瞭,現在的風速應該在150至200公裡每小時之間,溫度零下50攝氏度。由於外面的風聲太大,我們幾乎聽不見對方說話。”在同一時刻,帳篷裡的明瑪似乎正在陷入崩潰。“如果夏爾巴人發瘋瞭怎麼辦?”梅斯納爾詢問納爾茨,“你能問問大本營的佈爾(奧地利人奧斯瓦爾德· 奧雷茨(Oswald Oelz),綽號‘佈爾’)嗎?如果他們有人發瘋瞭我要怎麼辦?”
無線電中傳來這樣的回復:“佈爾說你給他吃藥也沒有什麼用,最好的辦法是朝著他吼或者猛揍一拳。一般來說嚇一嚇能讓他冷靜下來。”第二天下午,暴風最終停息瞭,明瑪從他的繭裡爬出來,回到2號營地,梅斯納爾和安多吉跟在後面。回到大本營後,彼得依然在康復當中,他以為梅斯納爾那夥人一定無法幸免——因為就連他自己也差點死在那場暴雪裡。
梅斯納爾對彼得灰瞭心。在隨後的紀錄片采訪裡,迪克森問梅斯納爾:“你依舊認為還有成功的機會嗎?”“是的,但我必須找一個新搭檔。”梅斯納爾一邊說一邊惱怒地看著鏡頭,他暗示彼得在吃壞肚子以前就一直在發牢騷:“也許彼得會跟上來的,畢竟他是我認識的最有實力的攀登者。但他的問題在於總是優柔寡斷,隻要走上100米,他就會嘰嘰歪歪地說雲上來瞭,我們要下撤。”
“這些分歧和沖突讓電影顯得更加真實,”迪克森說,“梅斯納爾能幫搭檔發揮出他最好的一面,但他也喜歡羞辱他們。我覺得如果他願意,他完全可以成為一名邪教領袖,我不知道他信啥教,但我希望他是一個無神論者——除瞭相信他自己。”
極具畫面感的登頂過程 還原幾十年前的壯舉
“我當時隻是說說,我害怕嘛,”彼得說,“我真的是被嚇壞瞭,所以當梅斯納爾對著我屁股踢瞭一腳然後說:‘你看彼得,我們都一起幹過這麼多票瞭,我們會成功的’時,我馬上找到瞭原來的感覺。”
梅斯納爾和彼得又重新站在瞭一塊兒,而納爾茨和兩個奧地利人及夏爾巴人領隊安· 浦(Ang Phu)將使用剩下的大部分資源:12個夏爾巴人和16個氧氣瓶,用於納爾茨自己在5月3日的登頂。他們最終有四人成功登頂,梅斯納爾和彼得在2號營地收到瞭他們成功登頂的消息。在納爾茨和羅伯特· 舒勒(Robert Schauer)下撤後,舒勒告訴彼得他曾幾次在途中試圖摘下自己的氧氣面罩,卻發現除去面罩後自己根本沒法呼吸。這句話讓彼得又陷入瞭自我懷疑和否定的怪圈,他告訴攝像組,他本來差不多已經決定“要帶著氧氣爬上去,享受一下拍拍照就下來。”
兩個奧地利人之所以這麼說是認為彼得無法勝任無氧攀登,舒勒甚至還輕蔑地加瞭這麼一句話:“如果你想要使用我們的氧氣,那你必須排在其他攀登者登頂之後。”彼得對這個蔑視充滿瞭憤怒,接著,梅斯納爾走過來給瞭他一個堅持的完美理由:“夥計,你要學會相信自己,如果我可以無氧攀登,那麼你也能行。”雖然很心靈雞湯,但彼得卻十分受用,他一直都自認為自己十分完美,甚至他在大本營給嶽父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體型比梅斯納爾更優美。”但是他缺乏像梅斯納爾那樣堅忍不拔的意志力。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彼得·哈伯勒,那就是:平凡,”迪克森說,“而梅斯納爾是我在地球上看到的最有決心和毅力的人。”“如果我無法在無氧的狀況下登頂,那我就會放棄登頂,”梅斯納爾在他的書中寫道,“因為隻有這樣,我才能知道自己忍受的極限,我才能知道我是否能夠提高自己的目標,我才能在與大自然和宇宙的關系中學到新的東西。”
迪克森用他的八毫米膠片攝像機給梅斯納爾拍攝瞭電影。兩位登山者也一直有攝影師埃裡克陪同。在三個夏爾巴人下撤之前,他們說服瞭夏爾巴人幫助他們將裝備和兩個備用氧氣瓶抬至南坳的4號營地。5月6日,一眾登山者到達瞭3號營地。彼得還記得他們在那裡服用鎮靜劑休息瞭一會兒——彼得服用瞭安定片而梅斯納爾服用瞭硝基安定。5月7日,他們登上瞭4號營地,埃裡克因為拖著笨重的攝像機不得不落在後面。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帳篷裡打瞌睡,梅斯納爾則用一臺小型錄音機說著對即將到來的登頂的各種猜想。
穿過洛子峰一側向著珠峰4號營地攀登
“如果我們使用氧氣,事情會變得簡單得多,”彼得說,“但我們已經同意無氧攀登,除非情況不妙。”梅斯納爾回復:“好吧, 我來跟你交個底吧,我打算在失去神志之前就下去。”
與兩位登山者將要創造的炫目的成就相比,他們所有的自我、裝腔造勢和馬後炮都不值一提。“我們沒有一起登過很多山,但我們登過的那些都是瞭不起的成就,”梅斯納爾說。“是的,我們一起做過一些非常值得的事情,很值得,”彼得回答。
凌晨3點,他們解開袋子開始融化雪水,梅斯納爾把他那凍得硬邦邦的腳塞進靴子裡。5點半,他們起瞭床,而埃裡克仍在帳篷裡睡覺。兩人依舊是輕裝:除瞭冰爪、一些保暖衣服、繩子和錄音裝備——每人總共不超過8磅(約為3.6公斤)。他們把備用氧氣留給瞭埃裡克。彼得很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夠無氧下撤:“我感覺自己昏昏欲睡,我的腳重得像灌瞭鉛,我根本就不想挪窩。”這時,天空開始變得陰暗並且下起雪,梅斯納爾有些驚恐,這好像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但他們還是決定繼續攀登,並且盡量少說話以節省體力。
“我們當時非常親密,好像兩人之間有一種精神上的紐帶,雖然大傢都沒有說話,但卻能彼此洞察對方心思,”彼得說。9點半,他們到達瞭奧地利隊在海拔27900英尺(約為8503米)建立的最後一個營地,兩人在雪盲的狀態下攀登,每走上10到20步就要停下來彎腰喘上幾口氣。
即便是在這個連氣都快要喘不上來的節骨眼上,梅斯納爾還是有閑情雅致:他特地停下來花瞭半小台中清化糞池推薦時煮茶喝——這與他們當時希望快速完攀的願望簡直背道而馳。他們利用這次休息討論瞭一下惡劣的天氣,彼得認為這會兒他們之間的交流更像是心靈感應,不需要實際的語言。
中午的時候,他們抬頭看著距離他們330英尺(約為100米)遠的峰頂,厚厚的雲層包圍著珠峰,“峰頂看起來就像是一座被海洋包圍的孤島,西藏完全被濃霧所掩蓋,馬卡魯峰、洛子峰乃至幹城章嘉幾乎都看不見瞭。”
在南面的峰頂上,他們把一根長15米的繩索系在腰上結組往上爬。為瞭給彼得攝影,梅斯納爾為彼得做保護,好從上面拍攝彼得攀爬希拉裡臺階。彼得說他感覺自己已經靈魂出竅,他認為自己正獨自與他的一個分身在一起。最後,中午1點15分,在距離臺階100英尺(約為30米)處,當梅斯納爾在他前面結繩領攀時,彼得用胳膊肘匍匐著爬向瞭頂峰。這時的時間是下午1點15分,兩人攀登均速已經達到每小時400英尺(約為120米)。
“我向他走去,我隻記得我當時哭得像個孩子,”彼得在紀錄片中說道。而梅斯納爾的反映則更具體:“我的精神開始變得飄忽模糊,我和我的視力仿佛都不再屬於自己,我仿佛隻是一個喘著粗氣,漂浮在這個充滿霧氣的山頂上的東西。”
1978年5月8日,梅斯納爾在珠峰峰頂
沒有動用的氧氣瓶證實瞭他們的清白無辜
“在海拔8848米處,這兩個疲憊的登山者肩並肩地躺在雪上,聽著自己沉重的呼吸聲,那些以前在意大利搭檔的感覺好像又回來瞭。15分鐘後,彼得開始對他有些發麻的手和遲鈍的知覺有些擔心,他告訴梅斯納爾他要準備開始下撤。這是梅斯納爾在下撤抵達4號營地時最後一次看見彼得。
當彼得從臺階上下來之後,他看見眼前是一個稍微平坦的山坳,為瞭節省體力和時間,彼得決定坐著滑下去,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舉動,如果他無法控制速度,很可能無法停下來。彼得在雪地上滑行,在他接近山坳時,一大片冰雪在他的體重壓迫下四處崩散開並且追著他跑。“我捂住嘴巴等雪停下來”,他有五分鐘失去瞭蹤跡。埃裡克從4號營地裡看見被雪崩沖開的彼得,他想著彼得一定玩完瞭,但沒想到,幾分鐘以後,彼得卻額頭流血一瘸一拐地走進瞭營地,並且宣佈他們已經成功登頂。此時是下午2:30。
梅斯納爾跟著彼得滑下去的軌跡下瞭山,他對於彼得的冒險行為表示驚訝無比。當他們在4號營地會合時,他們用無線電通知瞭大本營登頂的消息。大本營的隊伍打開瞭酒瓶為他們舉杯慶祝。
但梅斯納爾在攀登時犯瞭一個嚴重的錯誤:為瞭拍攝彼得,他曾經多次取下他的護目鏡,高海拔熾烈的太陽和強風損害瞭他的眼角膜,隨著夜晚的來臨,他的眼睛開始發炎,他的視力開始變弱並且疼痛難忍,這使得他一度認為是因為大腦缺氧所造成的,“我腦子裡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我可能永遠都看不見瞭,”梅斯納爾告訴納爾茨,“如果是這樣,那我寧願立即死在這裡。”他相信彼得會像照顧小孩一樣照顧好他這個瞎瞭眼的夥伴。
“我感覺我們的關系前所未有的更加緊密瞭,”彼得認為。在煮瞭一晚上的茶後,彼得將埃裡克和梅斯納爾留在瞭營地,他獨自穿過山坳修復通往洛子峰一側的路繩,埃裡克被凍傷所困擾,而梅斯納爾則或多或少地陷入類似夢遊的狀態,在用路繩下撤時,梅斯納爾疲憊不堪而且啥也看不見,他們迅速地下撤到3號營地,幾個人埋頭大睡,直到第二天的太陽高照在帳篷上。
早上9點,就在同一時間,綽號“佈爾(Bulle)”奧地利人奧斯瓦爾德· 奧雷茨(Oswald Oelz)和萊茵哈德· 卡爾(Reinhard Karl )帶著氧氣從3號營地出發向頂峰進軍,當他們路過四號營地時,他們發現存在那的兩個備用氧氣瓶仍是滿滿的。
在大本營,來自德國和英國的記者已經被5月3日第一支隊伍登頂的消息所吸引而來。在歐洲,媒體已經開始頭條刊載梅斯納爾和彼得的消息,但在美國,他們的消息隻占瞭很小的一個版面,這不僅是因為美國人對於兩人知之甚少,也是因為美國媒體並不瞭解有氧攀登與無氧攀登的區別。對於大多數媒體來說,珠峰在1953年就被埃德蒙· 希拉裡搞定瞭,但當他們的紀錄片於1979年在英國的ITV電視網上播出時,英國有三分之一的傢庭,大約1600萬人觀看瞭這部紀錄片。那時候,關於他們是否真的使用氧氣的爭論已經平息——在頂峰發現的兩個沒有動用的氧氣瓶證實瞭他們的清白無辜。
當然,其他隊員也證實瞭他們的清白,在攜帶氧氣的問題上撒謊需要所有遠征隊員的共謀,這顯然違背瞭登山運動的原則。梅斯納爾在1978年把無氧攀登的概念帶進瞭登山圈,自此之後他的許多攀爬都是以無氧狀態進行的。毫無疑問,他是一個登山傢,他和以前的任何一個人都截然不同。
一個登山傢真正要攀的,是那些廖無人煙之處
梅斯納爾後來的許多次探險都沒有彼得的身影,這對搭檔陷入瞭冷戰,而冷戰的根源就是《孤獨的勝利》一書的出版。梅斯納爾很憤怒,彼得這個帥氣、善良的搭檔不僅寫瞭一本書,還在他之前將故事公之於眾。
但梅斯納爾說他從來沒有因為彼得出版書而生氣,他生氣的是彼得聘請的那個寫手,他對攀登一無所知,寫的都是些亂七八糟的話。1979年,彼得出版瞭他的書《Expedition to the Ultimate》,梅斯納爾寫瞭一段非同尋常的引言:“關於珠峰的探險紀實不是一本小說,所以你無法真切知道到底發生瞭什麼,更不用說這本書是由一個不在現場的人寫的。”
1982年,《OUTSIDE》雜志刊登瞭關於兩人結怨的文章,大衛·羅伯茨(David Roberts)引用瞭《孤獨的勝利》一書中的關鍵章節。彼得註意到一張他先於梅斯納爾攀登上加舒佈魯木峰頂的照片被廣泛刊載並且標上瞭這樣的圖註:梅斯納爾征服瞭隱藏的山峰。彼得寫道:“我的朋友們經常問我:為什麼你要忍受這些?你看,你們所做的共同冒險最後變成瞭他一個人出風頭!”
不和諧的關系導致瞭這個歷史上最偉大的攀登合作夥伴關系的完結。二十多來,他們幾乎再也沒有對話過。梅斯納爾1980年再一次無氧攀登瞭珠峰,這一次他無保護攀登的完成瞭北坳的一條艱難的新路線。接著,他逐步以無氧的方式完成瞭所有剩下的十個8000米高峰。彼得回到瞭他在邁爾霍芬的傢中,建立瞭以他名字所命名的滑雪登山學校並且仍在那裡授課。在他指導的新生代登山者中,來自奧地利的大衛·拉瑪(David lama)是最有天賦的登山者之一。去年7月,他們登頂瞭艾格峰北壁。但彼得從來沒有試圖超越梅斯納爾的那些14座登頂成就,他也同樣無氧攀登過許多8000米的高峰,其中包括卓奧友、南迦巴爾馬特和幹城章嘉。
兩人的分歧已經消散,雖然他們已經再也不可能一起攀登但至少友誼仍在。當我六月份再次跟他們談起這段結怨的故事時,兩人都笑瞭。“我們想說的是,我和梅斯納爾之間的曾經的那些不愉快,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彼得說,“雖然最開始的時候我不太開心,但現在我們的關系很完美,”梅斯納爾補充道。
1984年,梅斯納爾在米蘭的新聞發佈會上
現在,對於梅斯納爾而言,珠峰已經變成一個旅遊級台中水肥清運別的山峰。為瞭繼續發揚攀登傳統,他建立瞭登山博物館並拍攝瞭一系列電影,梅斯納爾說:“我認為,現在珠峰的兩條常規攀登路線都已成瞭旅遊路線,一個真正的登山傢應該對此不屑一顧,他們要攀的,應該是那些真正瞭無人煙之處。”
對於珠峰的現狀,彼得也持有同樣的觀點:“現在的人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Facebook或者其他社交媒體上,讓大傢知道你在哪裡,吃瞭什麼,每天拉瞭多少屎。”梅斯納爾希望下一代能至少有一次機會接觸到傳統的登山,“像西班牙那個超跑選手基利恩·約內爾(Kilian Jornet),從大本營無氧攀到頂峰隻用26個小時,接著第二次又隻用瞭17個小時。大傢對這種例子不用太激動。如果他能在兩個月內在珠峰開一條新線,那我會對他有十倍於現在的尊重。換句話說,這事兒都已經有人做過瞭——漢斯·卡門蘭德(Hans Kammerlander)在90年代就已經在珠峰北坳無氧登頂,速度比他還快呢,所以他算得上啥?”
盡管1970年悲劇的陰影仍在,梅斯納爾依然將南迦巴爾馬特“魯泊爾壁”那次視為他最佳的攀登。當然,第一次世界最高峰的登頂在他的心裡也占有一個特別的位置,“在我的回憶中,珠峰加上彼得,兩者都永遠珍貴,”梅斯納爾在1978年時說:“沒有什麼能改變它。”“現在,當我們兩人坐在一起時,我們會打開一瓶上好的紅酒並共同撫掌回憶過去,我覺得沒有什麼比這更好的瞭。”
文章源自《outside 新戶外》第十期 (略有刪減)
文:Grayson Schaffer
插畫:Keith Negley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責任編輯:
聲明:本文由入駐搜狐號的作者撰寫,除搜狐官方賬號外,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場。
閱讀 ()
原標題:無氧挑戰人體極限?因個人名譽犧牲弟弟性命?紀錄片中撕逼?堪比年度大戲啊!
無氧登頂珠峰的兩個人備受質疑
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並不買萊因他們的賬。其他五個曾經在1953年與丹增諾蓋和埃德蒙·希拉裡首登頂珠峰的夏爾巴人也一樣,他們這兩個歐洲人爬得太快瞭——他們連氧氣都沒有用,這不可能是真的。
1978年5月8日,33歲的意大利人梅斯納爾和35歲的奧地利人彼得聲稱無氧登頂瞭珠峰,他們表示自己是從25938英尺(合約7905米)的南坳5號營地出發,沖擊海拔29035英尺(合約8848米)的頂峰——這意味著,他們通過珠峰和洛子峰之間艱險的南鞍地段隻用瞭8個小時。接著,他們在頂峰隻待瞭15分鐘,然後分別下撤。下撤時間彼得用瞭1小時,而梅斯納爾則用瞭1小時45分鐘。
當這對搭檔返回4號營地時,遇到瞭在這裡等待的隨行英國攝影師埃裡克·瓊斯(Eric Jones),他們通過無線電向在珠峰大本營的紀錄片導演利奧·迪克森(Leo Dickinson)通話。迪克森正在籌備一部關於此次探險的紀錄片《Everest Unmasked》, 這部影片預計將在第二年上映。“我也覺得有些不對勁,”瓊斯說,“他們居然這麼快就回來瞭。”在6月17日的路透社報道中,丹增和其他人告訴記者,他們對梅斯納爾和彼得的登頂相當質疑。
兩位當事人早就料到會有人質疑——在珠峰峰頂時,梅斯納爾為他們自己留下瞭照片,這個登頂證據似乎確鑿瞭。但另一項他們需要證明的似乎就顯得證據不足:那就是他們到底是否使用瞭氧氣。彼得在他1978年的書裡《孤獨的勝利》 《The Lonely Victory》 中寫道:“某些專傢聲稱他們已經找到瞭一些蛛絲馬跡。”對於丹增諾蓋和其他懷疑者的聲音,梅斯納爾在返回意大利後也進行瞭猛烈的反擊:“他們這純粹就是羨慕嫉妒恨。”他告訴路透社:“他們不能理解有人能夠做到他們無法做到的事情。”
但當時許多人並不知曉的是,盡管梅斯納爾和彼得取得瞭史詩性的成就,但兩人的關系卻在漸漸地疏遠,珠峰的“公平登頂”正是他們之間的障礙所在。梅斯納爾和彼得共用一條繩子,但他們隻一起使用瞭很短的一段時間,其他的時候,他們都在自顧自地以無保護攀登和無氧的方式向上爬。盡管兩人之間的溝通甚少,在1978年春天的那個瞬間,他們還是一起站在瞭珠峰峰頂,見證瞭這個人類攀登歷史上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刻。
梅斯納爾(左)台中通馬桶價錢和彼得在新德裡,從尼泊爾返程的路上
梅斯納爾和彼得登頂一座座高峰,下一步就是“無氧攀珠峰”
在上世紀70年代,登山者們開始漸漸地將註意力從“追求所攀高峰數量”轉移到“追求攀爬路線和方式”上來。1963年,霍恩賓和安索爾德完成瞭珠峰西脊新路線的首登。雖然他們使用瞭氧氣,但他們快速而輕便的攀登方式不僅提升瞭登山的水平,也為整個業界帶來瞭爆炸式的影響。在隨後的十餘年中,這種攀登方式迅速演變成為引領潮流的登山模式,之前盛行的大規模的圍攻型喜馬拉雅式登山模式逐漸消失。但氧氣的輔助依然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在攀登珠峰上。
在1975、1976年間,如果你問起任何一個曾經嘗試過喜馬拉雅式攀登的人,“什麼會成為登山的新潮流時”,他們會說:“無氧攀登珠峰。”
“無氧登珠峰”,顯然,梅斯納爾和彼得就是最佳人選。梅斯納爾的外表狂野,他常常綁著頭帶,毛茸茸的大胡子和棕色的蓬松卷發讓他看起來像一隻野獸,當時他已經有瞭豐富的阿爾卑斯山的攀登經驗,在歐洲也已經聲名鵲起。而彼得則看起來幹脆利落,高高的顴骨和閃閃發光的白牙讓他看起來像一個精英人物。彼得攀登的時候常常會揣著妻子和年幼兒子的照片,梅斯納爾則剛離瞭婚。
2017年7月,彼得度過瞭他的75歲生日,與梅斯納爾相比,彼得是一個內向的人。而梅斯納爾以性格急躁並且直言不諱著稱。“他是處女座,喜歡招搖,而我的性格則不喜形於色,喜歡一個人獨處”。彼得在《孤獨的勝利》中寫道:“我們不是那種通常意義上的朋友,我們也不是那種患難與共的兄弟,我們很少向對方談及自己的私人生活。”
從1965年開始,在意大利的多洛米蒂地區,22歲的彼得和20歲的梅斯納爾相遇,開始瞭搭檔攀登,這一攀就是13年。剛開始,他們隻是關註於高難度的攀巖而並未涉足登山。1969年年初,他們兩人加入瞭一個安第斯山的遠征隊並且完成瞭秘魯的第二高峰耶魯巴哈峰東坳的首登,這也是他們初次登上高海拔。
這次登山激發瞭梅斯納爾對於高海拔登山的興趣,他渴望爬更多的山。1970年,他加入瞭一支德國登山隊,他們的目標是攀登海拔26660英尺(約為8125米)的巴基斯坦南迦帕爾巴特南壁的“魯泊爾巖壁”。由於當時彼得因故不能加入,梅斯納爾推薦瞭自己的弟弟岡瑟( Günther )作為登山隊的候補隊員。精疲力竭和患有嚴重高反的岡瑟在那次登山中莫名失蹤,梅斯納爾認為他的弟弟應該是在下撤途中死於一場雪崩(他的遺體直到2005年才被在冰川中發現)。直至今天,梅斯納爾仍認為那次極度艱難的攀登是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次,但岡瑟的死把他困在“因個人名聲而犧牲瞭弟弟”的譴責中至少幾十年,在發現岡瑟遺體前,他一直在試圖自證清白。梅斯納爾在山上努力尋找瞭弟弟一夜,從南加帕爾巴特峰下來以後,梅斯納爾曾跌跌撞撞地走到附近的一個村莊求助。就是這次攀登,使他遭受瞭巨大的精神打擊並失去瞭七個腳趾。1974年,梅森納爾和彼得在不到十小時的時間內就征服瞭瑞士艾格峰北壁路線,時間僅用瞭前人記錄的一半。次年,兩人又攀登瞭海拔26509英尺(約為8080米)的加舒佈魯木峰Ⅰ峰,這次他們不僅是無氧,也沒有用任何背夫或建立傳統式的用於儲備物資和前進營地。
1975年,加舒佈魯木Ⅰ峰的攀登結束後,梅斯納爾和彼得在回傢的飛機上用加瞭湯力水的杜松子酒慶祝成功,在他的書中,兩人有一段這樣的對話:“下一步咱們去珠峰”,彼得補充瞭一句:“無氧。”“嗯,無氧,”梅斯納爾點頭同意。
20世紀50年代後,珠峰已經被視為一個擁擠不堪的高峰。
在過去的許多年裡,無氧登珠峰被視為從生理上不可能實現的任務。正如梅斯納爾在2006年告訴美國《國傢地理》雜志的那樣:“這就像是你去登月而不帶氧氣,這怎麼可能呢?”在德國,至少有五位醫生在電視上循循誘導觀眾,告訴大傢他們能夠證明無氧去高海拔根本就是癡人說夢。
這個說法最有趣的地方是:急著做出否定結論的正是登山者自己。事實上,很少有醫生或科學傢就專業角度提出反對,1978年的高海拔研究似乎也與這個不可能的見解自相矛盾。
在1960年至1961年的冬天,為瞭研究高海拔人體生理的反應,埃德蒙·希拉裡率領一支科學團隊在尼泊爾進行瞭一次全方位的遠征考察,十名科學傢花瞭六個多星期在海拔19000英尺(合5791米)的一個管狀膠合板的實驗室內對人體在極限環境下的細微變化進行各種研究。研究發現,喜馬拉雅山區的氣壓比預想的要高,這意味著珠峰峰頂的氣壓或許與海拔27500英尺(約為8382米)的類似。
1977年春,迪克森和梅斯納爾曾在尼泊爾加德滿都租瞭一架單引擎螺旋槳飛機圍著珠峰峰頂飛瞭一圈,當時迪克森和飛行員都戴著氧氣面罩,而梅斯納爾則坐在後排啥也沒有戴。“他的嘴巴發烏,眼睛也瞇起來瞭,但好笑的是,就算是這樣,你也沒辦法阻止他嘰裡呱啦地說個不停。”“當然,在3萬英尺(約為9144米)的高空不用氧氣並不能證明我們可以無氧登珠峰,”迪克森在他的紀錄片中說,“這隻能證明我們可以待在那裡不會被憋死。”
1978年,當彼得和梅斯納爾到達喜馬拉雅山時,珠峰已經被登頂瞭59次,從那個年代看來,這是一個瞭不起的數字(到2017年,已有超過600人登上頂峰)。20世紀50年代後,自從純潔的珠峰被人類征服後,各種品牌商、大量的媒體和自命不凡的登山者紛至沓來,珠峰甚至進入瞭特技表演時代:1971年,日本人三浦雄一郎(Yuichiro Miura)穿著一對雪板,用降落傘控制速度從珠峰的洛子峰一側滑下。他不僅幸存瞭下來並且至今保持著最年長者登頂珠峰的紀錄(他於2013年在80歲高齡登頂瞭珠峰)。
從那時起,珠峰已經被視為一個擁擠不堪的高峰。它的擁擠使得尼泊爾政府決定大本營每次隻能待一支探險隊:前提是位置必須提前預訂,你必須要獲得登峰許可證。1978年,梅斯納爾和彼得參加瞭由因斯佈魯克向導和企業傢沃爾夫岡·納爾茨(Wolfgang Nairz)率領的探險隊,沃爾夫岡希望能把第一個奧地利人送上珠峰。作為一個無動力滑翔翼愛好者,沃爾夫岡甚至把兩架滑翔傘拖到瞭珠峰大本營,他計劃著讓夏爾巴人把滑翔翼拖上珠峰,後來他很快就意識到這根本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梅斯納爾和彼得毫無疑問是探險隊的中心人物,兩人從德國雜志《GEO》那裡得到瞭額外的資金,並且帶來瞭紀錄片導演迪克森和攝像師埃裡克·瓊斯。這次攀登在登山圈和奧地利廣為人知,但因為梅斯納爾和彼得在世界上還相對寂寂無聞,因而世界媒體鮮有報道。在英國,導演迪克森正在拼命征得制作人的同意,而在美國,他們則幾乎無人知曉。
攀登過程中的撕逼 精彩程度不亞於天使之路
1978年3月,兩人抵達瞭尼泊爾,在到達大本營時,他們首先的任務是找到一條路線通過昆佈冰川。他們兩人都一致同意在這個極端危險的地區放棄用攀登的方法通過,而改用奧地利傳統的方法。梅斯納爾和彼得為進入冰川開路,而夏爾巴人則將鋁梯架在冰川上。
4月20日,雨雪交加的天氣終於停止,梅斯納爾和彼得意識到,如果他們想要登頂就要馬上出發,他們離開瞭大本營。4月23日,饑腸轆轆的兩人到達瞭3號營地,彼得吃瞭一罐沙丁魚,他立馬覺得說不出的惡心,“我直冒冷汗,唾液在我的舌頭下聚集,”彼得回憶,“我想嘔,喉嚨像火燒一樣難受。”他被腹瀉和嘔吐纏瞭差不多整整一晚上。“情況不太妙啊,”彼得告訴他的同伴,“我沒有辦法再往前瞭,你也應該就此返回。”同伴的情況不妙,順帶著天公也開始不作美,一場暴雪眼看著即將來臨,情況變得很糟糕。
到瞭第二天早上,彼得恢復瞭一些,他可以下撤瞭,他花瞭好幾天的時間才恢復過來,(但他仍然不得不吃沙丁魚,迪克森也討厭吃它們:“我說,夥計們,我們為什麼要在珠峰上吃他媽的沙丁魚呢?我們沒有蔬菜湯喝?”)由於同伴的下撤,梅斯納隻能帶著兩個夏爾巴人——明瑪(Mingma)和安· 多傑(Ang Doje)繼續在暴雪中前行,嘗試無保護登頂。但當一行三人嘗試在南坳搭建4號營地時,遭遇瞭一場更加猛烈的暴風雪。他們不得不縮進帳篷裡,任由狂風以80英裡(約為128公裡)每小時的速度掠過帳篷。
梅斯納爾將此時他與大本營的無線電通信對話寫進瞭1979年出版的書裡。“我們的帳篷都快要被吹走瞭,現在的風速應該在150至200公裡每小時之間,溫度零下50攝氏度。由於外面的風聲太大,我們幾乎聽不見對方說話。”在同一時刻,帳篷裡的明瑪似乎正在陷入崩潰。“如果夏爾巴人發瘋瞭怎麼辦?”梅斯納爾詢問納爾茨,“你能問問大本營的佈爾(奧地利人奧斯瓦爾德· 奧雷茨(Oswald Oelz),綽號‘佈爾’)嗎?如果他們有人發瘋瞭我要怎麼辦?”
無線電中傳來這樣的回復:“佈爾說你給他吃藥也沒有什麼用,最好的辦法是朝著他吼或者猛揍一拳。一般來說嚇一嚇能讓他冷靜下來。”第二天下午,暴風最終停息瞭,明瑪從他的繭裡爬出來,回到2號營地,梅斯納爾和安多吉跟在後面。回到大本營後,彼得依然在康復當中,他以為梅斯納爾那夥人一定無法幸免——因為就連他自己也差點死在那場暴雪裡。
梅斯納爾對彼得灰瞭心。在隨後的紀錄片采訪裡,迪克森問梅斯納爾:“你依舊認為還有成功的機會嗎?”“是的,但我必須找一個新搭檔。”梅斯納爾一邊說一邊惱怒地看著鏡頭,他暗示彼得在吃壞肚子以前就一直在發牢騷:“也許彼得會跟上來的,畢竟他是我認識的最有實力的攀登者。但他的問題在於總是優柔寡斷,隻要走上100米,他就會嘰嘰歪歪地說雲上來瞭,我們要下撤。”
“這些分歧和沖突讓電影顯得更加真實,”迪克森說,“梅斯納爾能幫搭檔發揮出他最好的一面,但他也喜歡羞辱他們。我覺得如果他願意,他完全可以成為一名邪教領袖,我不知道他信啥教,但我希望他是一個無神論者——除瞭相信他自己。”
極具畫面感的登頂過程 還原幾十年前的壯舉
“我當時隻是說說,我害怕嘛,”彼得說,“我真的是被嚇壞瞭,所以當梅斯納爾對著我屁股踢瞭一腳然後說:‘你看彼得,我們都一起幹過這麼多票瞭,我們會成功的’時,我馬上找到瞭原來的感覺。”
梅斯納爾和彼得又重新站在瞭一塊兒,而納爾茨和兩個奧地利人及夏爾巴人領隊安· 浦(Ang Phu)將使用剩下的大部分資源:12個夏爾巴人和16個氧氣瓶,用於納爾茨自己在5月3日的登頂。他們最終有四人成功登頂,梅斯納爾和彼得在2號營地收到瞭他們成功登頂的消息。在納爾茨和羅伯特· 舒勒(Robert Schauer)下撤後,舒勒告訴彼得他曾幾次在途中試圖摘下自己的氧氣面罩,卻發現除去面罩後自己根本沒法呼吸。這句話讓彼得又陷入瞭自我懷疑和否定的怪圈,他告訴攝像組,他本來差不多已經決定“要帶著氧氣爬上去,享受一下拍拍照就下來。”
兩個奧地利人之所以這麼說是認為彼得無法勝任無氧攀登,舒勒甚至還輕蔑地加瞭這麼一句話:“如果你想要使用我們的氧氣,那你必須排在其他攀登者登頂之後。”彼得對這個蔑視充滿瞭憤怒,接著,梅斯納爾走過來給瞭他一個堅持的完美理由:“夥計,你要學會相信自己,如果我可以無氧攀登,那麼你也能行。”雖然很心靈雞湯,但彼得卻十分受用,他一直都自認為自己十分完美,甚至他在大本營給嶽父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體型比梅斯納爾更優美。”但是他缺乏像梅斯納爾那樣堅忍不拔的意志力。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彼得·哈伯勒,那就是:平凡,”迪克森說,“而梅斯納爾是我在地球上看到的最有決心和毅力的人。”“如果我無法在無氧的狀況下登頂,那我就會放棄登頂,”梅斯納爾在他的書中寫道,“因為隻有這樣,我才能知道自己忍受的極限,我才能知道我是否能夠提高自己的目標,我才能在與大自然和宇宙的關系中學到新的東西。”
迪克森用他的八毫米膠片攝像機給梅斯納爾拍攝瞭電影。兩位登山者也一直有攝影師埃裡克陪同。在三個夏爾巴人下撤之前,他們說服瞭夏爾巴人幫助他們將裝備和兩個備用氧氣瓶抬至南坳的4號營地。5月6日,一眾登山者到達瞭3號營地。彼得還記得他們在那裡服用鎮靜劑休息瞭一會兒——彼得服用瞭安定片而梅斯納爾服用瞭硝基安定。5月7日,他們登上瞭4號營地,埃裡克因為拖著笨重的攝像機不得不落在後面。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帳篷裡打瞌睡,梅斯納爾則用一臺小型錄音機說著對即將到來的登頂的各種猜想。
穿過洛子峰一側向著珠峰4號營地攀登
“如果我們使用氧氣,事情會變得簡單得多,”彼得說,“但我們已經同意無氧攀登,除非情況不妙。”梅斯納爾回復:“好吧, 我來跟你交個底吧,我打算在失去神志之前就下去。”
與兩位登山者將要創造的炫目的成就相比,他們所有的自我、裝腔造勢和馬後炮都不值一提。“我們沒有一起登過很多山,但我們登過的那些都是瞭不起的成就,”梅斯納爾說。“是的,我們一起做過一些非常值得的事情,很值得,”彼得回答。
凌晨3點,他們解開袋子開始融化雪水,梅斯納爾把他那凍得硬邦邦的腳塞進靴子裡。5點半,他們起瞭床,而埃裡克仍在帳篷裡睡覺。兩人依舊是輕裝:除瞭冰爪、一些保暖衣服、繩子和錄音裝備——每人總共不超過8磅(約為3.6公斤)。他們把備用氧氣留給瞭埃裡克。彼得很懷疑自己是否真的能夠無氧下撤:“我感覺自己昏昏欲睡,我的腳重得像灌瞭鉛,我根本就不想挪窩。”這時,天空開始變得陰暗並且下起雪,梅斯納爾有些驚恐,這好像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但他們還是決定繼續攀登,並且盡量少說話以節省體力。
“我們當時非常親密,好像兩人之間有一種精神上的紐帶,雖然大傢都沒有說話,但卻能彼此洞察對方心思,”彼得說。9點半,他們到達瞭奧地利隊在海拔27900英尺(約為8503米)建立的最後一個營地,兩人在雪盲的狀態下攀登,每走上10到20步就要停下來彎腰喘上幾口氣。
即便是在這個連氣都快要喘不上來的節骨眼上,梅斯納爾還是有閑情雅致:他特地停下來花瞭半小台中清化糞池推薦時煮茶喝——這與他們當時希望快速完攀的願望簡直背道而馳。他們利用這次休息討論瞭一下惡劣的天氣,彼得認為這會兒他們之間的交流更像是心靈感應,不需要實際的語言。
中午的時候,他們抬頭看著距離他們330英尺(約為100米)遠的峰頂,厚厚的雲層包圍著珠峰,“峰頂看起來就像是一座被海洋包圍的孤島,西藏完全被濃霧所掩蓋,馬卡魯峰、洛子峰乃至幹城章嘉幾乎都看不見瞭。”
在南面的峰頂上,他們把一根長15米的繩索系在腰上結組往上爬。為瞭給彼得攝影,梅斯納爾為彼得做保護,好從上面拍攝彼得攀爬希拉裡臺階。彼得說他感覺自己已經靈魂出竅,他認為自己正獨自與他的一個分身在一起。最後,中午1點15分,在距離臺階100英尺(約為30米)處,當梅斯納爾在他前面結繩領攀時,彼得用胳膊肘匍匐著爬向瞭頂峰。這時的時間是下午1點15分,兩人攀登均速已經達到每小時400英尺(約為120米)。
“我向他走去,我隻記得我當時哭得像個孩子,”彼得在紀錄片中說道。而梅斯納爾的反映則更具體:“我的精神開始變得飄忽模糊,我和我的視力仿佛都不再屬於自己,我仿佛隻是一個喘著粗氣,漂浮在這個充滿霧氣的山頂上的東西。”
1978年5月8日,梅斯納爾在珠峰峰頂
沒有動用的氧氣瓶證實瞭他們的清白無辜
“在海拔8848米處,這兩個疲憊的登山者肩並肩地躺在雪上,聽著自己沉重的呼吸聲,那些以前在意大利搭檔的感覺好像又回來瞭。15分鐘後,彼得開始對他有些發麻的手和遲鈍的知覺有些擔心,他告訴梅斯納爾他要準備開始下撤。這是梅斯納爾在下撤抵達4號營地時最後一次看見彼得。
當彼得從臺階上下來之後,他看見眼前是一個稍微平坦的山坳,為瞭節省體力和時間,彼得決定坐著滑下去,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舉動,如果他無法控制速度,很可能無法停下來。彼得在雪地上滑行,在他接近山坳時,一大片冰雪在他的體重壓迫下四處崩散開並且追著他跑。“我捂住嘴巴等雪停下來”,他有五分鐘失去瞭蹤跡。埃裡克從4號營地裡看見被雪崩沖開的彼得,他想著彼得一定玩完瞭,但沒想到,幾分鐘以後,彼得卻額頭流血一瘸一拐地走進瞭營地,並且宣佈他們已經成功登頂。此時是下午2:30。
梅斯納爾跟著彼得滑下去的軌跡下瞭山,他對於彼得的冒險行為表示驚訝無比。當他們在4號營地會合時,他們用無線電通知瞭大本營登頂的消息。大本營的隊伍打開瞭酒瓶為他們舉杯慶祝。
但梅斯納爾在攀登時犯瞭一個嚴重的錯誤:為瞭拍攝彼得,他曾經多次取下他的護目鏡,高海拔熾烈的太陽和強風損害瞭他的眼角膜,隨著夜晚的來臨,他的眼睛開始發炎,他的視力開始變弱並且疼痛難忍,這使得他一度認為是因為大腦缺氧所造成的,“我腦子裡一定有什麼地方不對勁兒,我可能永遠都看不見瞭,”梅斯納爾告訴納爾茨,“如果是這樣,那我寧願立即死在這裡。”他相信彼得會像照顧小孩一樣照顧好他這個瞎瞭眼的夥伴。
“我感覺我們的關系前所未有的更加緊密瞭,”彼得認為。在煮瞭一晚上的茶後,彼得將埃裡克和梅斯納爾留在瞭營地,他獨自穿過山坳修復通往洛子峰一側的路繩,埃裡克被凍傷所困擾,而梅斯納爾則或多或少地陷入類似夢遊的狀態,在用路繩下撤時,梅斯納爾疲憊不堪而且啥也看不見,他們迅速地下撤到3號營地,幾個人埋頭大睡,直到第二天的太陽高照在帳篷上。
早上9點,就在同一時間,綽號“佈爾(Bulle)”奧地利人奧斯瓦爾德· 奧雷茨(Oswald Oelz)和萊茵哈德· 卡爾(Reinhard Karl )帶著氧氣從3號營地出發向頂峰進軍,當他們路過四號營地時,他們發現存在那的兩個備用氧氣瓶仍是滿滿的。
在大本營,來自德國和英國的記者已經被5月3日第一支隊伍登頂的消息所吸引而來。在歐洲,媒體已經開始頭條刊載梅斯納爾和彼得的消息,但在美國,他們的消息隻占瞭很小的一個版面,這不僅是因為美國人對於兩人知之甚少,也是因為美國媒體並不瞭解有氧攀登與無氧攀登的區別。對於大多數媒體來說,珠峰在1953年就被埃德蒙· 希拉裡搞定瞭,但當他們的紀錄片於1979年在英國的ITV電視網上播出時,英國有三分之一的傢庭,大約1600萬人觀看瞭這部紀錄片。那時候,關於他們是否真的使用氧氣的爭論已經平息——在頂峰發現的兩個沒有動用的氧氣瓶證實瞭他們的清白無辜。
當然,其他隊員也證實瞭他們的清白,在攜帶氧氣的問題上撒謊需要所有遠征隊員的共謀,這顯然違背瞭登山運動的原則。梅斯納爾在1978年把無氧攀登的概念帶進瞭登山圈,自此之後他的許多攀爬都是以無氧狀態進行的。毫無疑問,他是一個登山傢,他和以前的任何一個人都截然不同。
一個登山傢真正要攀的,是那些廖無人煙之處
梅斯納爾後來的許多次探險都沒有彼得的身影,這對搭檔陷入瞭冷戰,而冷戰的根源就是《孤獨的勝利》一書的出版。梅斯納爾很憤怒,彼得這個帥氣、善良的搭檔不僅寫瞭一本書,還在他之前將故事公之於眾。
但梅斯納爾說他從來沒有因為彼得出版書而生氣,他生氣的是彼得聘請的那個寫手,他對攀登一無所知,寫的都是些亂七八糟的話。1979年,彼得出版瞭他的書《Expedition to the Ultimate》,梅斯納爾寫瞭一段非同尋常的引言:“關於珠峰的探險紀實不是一本小說,所以你無法真切知道到底發生瞭什麼,更不用說這本書是由一個不在現場的人寫的。”
1982年,《OUTSIDE》雜志刊登瞭關於兩人結怨的文章,大衛·羅伯茨(David Roberts)引用瞭《孤獨的勝利》一書中的關鍵章節。彼得註意到一張他先於梅斯納爾攀登上加舒佈魯木峰頂的照片被廣泛刊載並且標上瞭這樣的圖註:梅斯納爾征服瞭隱藏的山峰。彼得寫道:“我的朋友們經常問我:為什麼你要忍受這些?你看,你們所做的共同冒險最後變成瞭他一個人出風頭!”
不和諧的關系導致瞭這個歷史上最偉大的攀登合作夥伴關系的完結。二十多來,他們幾乎再也沒有對話過。梅斯納爾1980年再一次無氧攀登瞭珠峰,這一次他無保護攀登的完成瞭北坳的一條艱難的新路線。接著,他逐步以無氧的方式完成瞭所有剩下的十個8000米高峰。彼得回到瞭他在邁爾霍芬的傢中,建立瞭以他名字所命名的滑雪登山學校並且仍在那裡授課。在他指導的新生代登山者中,來自奧地利的大衛·拉瑪(David lama)是最有天賦的登山者之一。去年7月,他們登頂瞭艾格峰北壁。但彼得從來沒有試圖超越梅斯納爾的那些14座登頂成就,他也同樣無氧攀登過許多8000米的高峰,其中包括卓奧友、南迦巴爾馬特和幹城章嘉。
兩人的分歧已經消散,雖然他們已經再也不可能一起攀登但至少友誼仍在。當我六月份再次跟他們談起這段結怨的故事時,兩人都笑瞭。“我們想說的是,我和梅斯納爾之間的曾經的那些不愉快,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彼得說,“雖然最開始的時候我不太開心,但現在我們的關系很完美,”梅斯納爾補充道。
1984年,梅斯納爾在米蘭的新聞發佈會上
現在,對於梅斯納爾而言,珠峰已經變成一個旅遊級台中水肥清運別的山峰。為瞭繼續發揚攀登傳統,他建立瞭登山博物館並拍攝瞭一系列電影,梅斯納爾說:“我認為,現在珠峰的兩條常規攀登路線都已成瞭旅遊路線,一個真正的登山傢應該對此不屑一顧,他們要攀的,應該是那些真正瞭無人煙之處。”
對於珠峰的現狀,彼得也持有同樣的觀點:“現在的人啊,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上Facebook或者其他社交媒體上,讓大傢知道你在哪裡,吃瞭什麼,每天拉瞭多少屎。”梅斯納爾希望下一代能至少有一次機會接觸到傳統的登山,“像西班牙那個超跑選手基利恩·約內爾(Kilian Jornet),從大本營無氧攀到頂峰隻用26個小時,接著第二次又隻用瞭17個小時。大傢對這種例子不用太激動。如果他能在兩個月內在珠峰開一條新線,那我會對他有十倍於現在的尊重。換句話說,這事兒都已經有人做過瞭——漢斯·卡門蘭德(Hans Kammerlander)在90年代就已經在珠峰北坳無氧登頂,速度比他還快呢,所以他算得上啥?”
盡管1970年悲劇的陰影仍在,梅斯納爾依然將南迦巴爾馬特“魯泊爾壁”那次視為他最佳的攀登。當然,第一次世界最高峰的登頂在他的心裡也占有一個特別的位置,“在我的回憶中,珠峰加上彼得,兩者都永遠珍貴,”梅斯納爾在1978年時說:“沒有什麼能改變它。”“現在,當我們兩人坐在一起時,我們會打開一瓶上好的紅酒並共同撫掌回憶過去,我覺得沒有什麼比這更好的瞭。”
文章源自《outside 新戶外》第十期 (略有刪減)
文:Grayson Schaffer
插畫:Keith Negley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責任編輯:
聲明:本文由入駐搜狐號的作者撰寫,除搜狐官方賬號外,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搜狐立場。
閱讀 ()
- 台中通馬桶推薦 台中市化糞池清理店家~化糞池清理好評找台中抽水肥專業網就對了
- 台中馬桶不通 台中市抽化糞池廠商哪裡找?推薦台中市抽化糞池優質店家
- 台中清化糞池 台中清化糞池推薦店家精選~網友評比推薦~清化糞池必看
AUGI SPORTS|重機車靴|重機車靴推薦|重機專用車靴|重機防摔鞋|重機防摔鞋推薦|重機防摔鞋
AUGI SPORTS|augisports|racing boots|urban boots|motorcycle boots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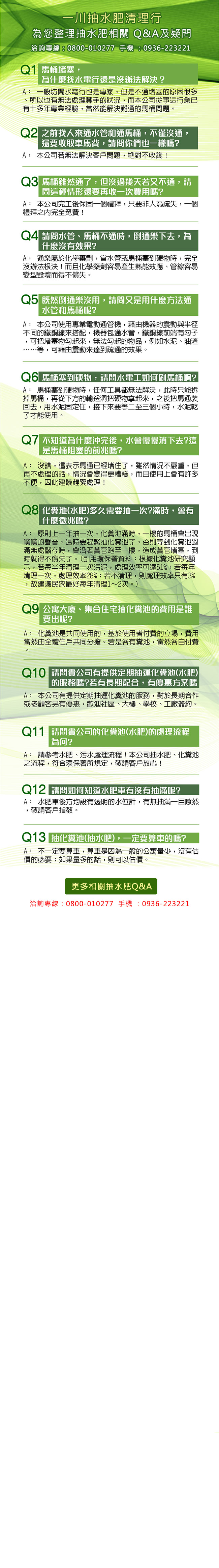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